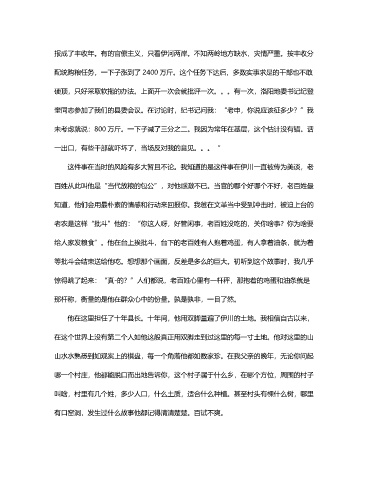Page 7 - tmp
P. 7
报成了丰收年。有的官僚主义,只看伊河两岸。不知两岭地方缺水,灾情严重。按丰收分
配统购粮任务,一下子涨到了 2400 万斤。这个任务下达后,多数实事求是的干部也不敢
硬顶,只好采取软拖的办法。上面开一次会就批评一次。。。有一次,洛阳地委书记纪登
奎同志参加了我们的县委会议。在讨论时,纪书记问我:“老申,你说应该征多少?”我
未考虑就说:800 万斤。一下子减了三分之二。我因为常年在基层,这个估计没有错。话
一出口,有些干部就吓坏了,当场反对我的意见。。。“
这件事在当时的风险有多大暂且不论。我知道的是这件事在伊川一直被传为美谈,老
百姓从此叫他是“当代放粮的包公”,对他感激不已。当官的哪个好哪个不好,老百姓最
知道,他们会用最朴素的情感和行动来回报你。我爸在文革当中受到冲击时,被迫上台的
老农是这样“批斗”他的:“你这人呀,好管闲事,老百姓没吃的,关你啥事?你为啥要
给人家发粮食”。他在台上挨批斗,台下的老百姓有人抱着鸡蛋,有人拿着油条,就为着
等批斗会结束送给他吃。想想那个画面,反差是多么的巨大。初听到这个故事时,我几乎
惊得跳了起来:“真-的?”人们都说,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那抱着的鸡蛋和油条就是
那杆称,衡量的是他在群众心中的份量。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他在这里担任了十年县长。十年间,他用双脚量遍了伊川的土地。我相信自古以来,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如他这般真正用双脚走到过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他对这里的山
山水水熟悉到如观案上的棋盘,每一个角落他都如数家珍。在我父亲的晚年,无论你问起
哪一个村庄,他都能脱口而出地告诉你,这个村子属于什么乡,在哪个方位,周围的村子
叫啥,村里有几个姓,多少人口,什么土质,适合什么种植。甚至村头有棵什么树,哪里
有口窑洞,发生过什么故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百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