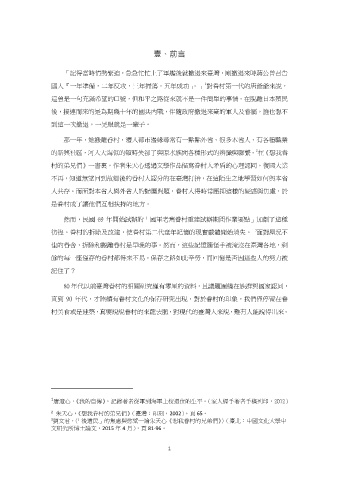Page 5 - final0629
P. 5
壹、前言
「記得當時情勢緊迫,急急忙忙上了軍艦後就撤退來臺灣,剛撤退來時蔣公曾召告
1
國人『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 對眷村第一代的唐爺爺來說,
這曾是一句充滿希望的口號,但和平之路從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脫離日本殖民
後,接連而來的是為期幾十年的國共內戰,伴隨政府撤退來臺的軍人及眷屬,誰也想不
到這一次撤退,一晃眼就是一輩子。
那一年,她搬離眷村,遷入都市邊緣尋常有一點點外省、很多本省人、有各種職業
2
的新興社區,河入大海似的頓時失卻了與原水族間各種形式的辨識與聯繫。 在《想我眷
村的弟兄們》一書裏,作者朱天心透過文學作品描寫眷村人矛盾的心理認同。復國大業
不再,知道無望回到故鄉後的眷村人認分的在臺灣打拚,在這陌生之地學習如何與本省
人共存。而面對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歸屬問題,眷村人得時常壓抑這樣的疑惑與焦慮,於
是眷村成了讓他們互相扶持的地方。
然而,民國 69 年開始試辦的「國軍老舊眷村重建試辦期間作業要點」加劇了這種
3
彷徨。眷村的拆除及改建,使眷村第二代童年記憶的現實載體開始消失。 面對屋況不
佳的眷舍,拆除和搬離眷村是早晚的事。然而,這些記憶隨怪手被淹沒在臺灣各地,剩
餘的每一座僅存的眷村都得來不易。保存之路如此辛勞,而回憶是否因這些人的努力被
記住了?
80 年代以前臺灣眷村的相關研究僅有零星的資料,且議題圍繞在族群與國家認同,
直到 90 年代,才陸續有眷村文化的保存研究出現,對於眷村的印象,我們僅停留在眷
村美食或是建築,真要說說眷村的來龍去脈,對現代的臺灣人來說,難有人能說得出來。
1 唐澄心,《我的自傳》,記錄著者從軍到海軍上校退位的生平。(家人經手著者手稿列印,2012)
2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弟兄們》( 臺灣:印刻,2002), 頁 65。
3 劉文君,〈「後遺民」的焦慮與慾望─論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
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15 年 4 月),頁 81-96。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