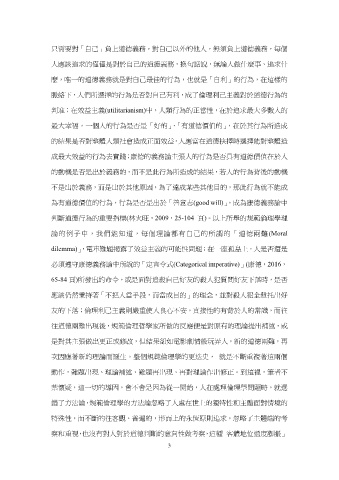Page 418 - 107學年度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畢業專題發表會「向。哲光」
P. 418
只需要對「自己」負上道德義務,對自己以外的他人,無須負上道德義務,每個
人應該追求的僅僅是對於自己的道德義務,換句話說,無論人做什麼事、追求什
麼,唯一的道德義務就是對自己最佳的行為,也就是「自利」的行為,在這樣的
脈絡下,人們所選擇的行為是否對自己有利,成了倫理利己主義對於道德行為的
判准;在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中,人類行為的正當性,在於追求最大多數人的
最大幸福,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是「好的」、「有道德價值的」,在於其行為所造成
的結果是否對整體人類社會造成正面效益,人應當在道德抉擇時選擇能對整體造
成最大效益的行為去實踐;康德的義務論主張人的行為是否具有道德價值在於人
的動機是否是出於義務的,而不是此行為所造成的結果,若人的行為背後的動機
不是出於義務,而是出於其他原因,為了達成某些其他目的,那此行為就不能成
為有道德價值的行為,行為是否是出於「善意志(good will)」,成為康德義務論中
判斷道德行為的重要指標(林火旺,2009,25-104 頁)。以上所舉的規範倫理學理
論的例子中,我們能知道,每個理論都有自己的所謂的「道德兩難(Moral
dilemma)」,電車難題揭露了效益主義的可能性問題;在一座孤島上,人是否還是
必須遵守康德義務論中所說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康德,2016,
65-84 頁)所發出的命令,或是面對追殺自己好友的殺人犯質問好友下落時,是否
應該仍然秉持著「不把人當手段,而當成目的」的理念,並對殺人犯全盤托出好
友的下落;倫理利己主義則嚴重使人良心不安,直接性的有背於人的常識,而往
往道德兩難出現後,規範倫理哲學家所做的反應便是對原有的理論提出補述,或
是對其主張做出更正或修改,但結果卻如電影劇情般玩弄人,新的道德兩難,再
次因應著新的理論而誕生,整個規範倫理學的更迭史, 就是不斷重複著這兩個
動作,難題出現、理論補述、難題再出現、再對理論作出修正。到這裡,筆者不
禁懷疑,這一切的導因,會不會是因為從一開始,人在處理倫理學問題時,就選
錯了方法論,規範倫理學的方法論忽略了人處在世上的獨特性和主體面對情境的
特殊性,而不斷的往客觀、普遍的,形而上的永恆原則追求,忽略了主體端的考
察和重視,也沒有對人對於道德判斷的意向性做考察,這種「客體地位過度膨脹」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