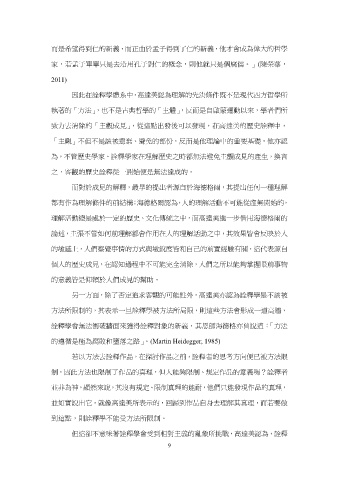Page 504 - 107學年度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畢業專題發表會「向。哲光」
P. 504
而是希望得到仁的新義,而正由於孟子得到了仁的新義,他才會成為偉大的哲學
家,若孟子單單只是去沿用孔子對仁的概念,則他就只是個腐儒。」(陳榮華,
2011)
因此在詮釋學體系中,高達美認為理解的先決條件既不是現代西方哲學所
執著的「方法」,也不是古典哲學的「主體」,反而是自啟蒙運動以來,學者們所
致力去清除的「主觀成見」,從這點出發後可以發現,在高達美的歷史詮釋中,
「主觀」不但不是該被遺棄、避免的部份,反而是他理論中的重要基礎,他亦認
為,不管歷史學家、詮釋學家在理解歷史之時都無法避免主觀成見的產生,換言
之,客觀的歷史詮釋從一開始便是無法達成的。
而對於成見的解釋,最早的提出者源自於海德格爾,其提出任何一種理解
都有作為理解條件的前結構;海德格爾認為,人的理解活動不可能從虛無開始的,
理解活動總是處於一定的歷史、文化傳統之中,而高達美進一步借用海德格爾的
論述,主張不管如何前理解都會作用在人的理解活動之中,其效果皆會反映於人
的敏感上 , 人們察覺事情的方式與敏銳度皆和自己的前置經驗有關,這代表源自
個人的歷史成見,在認知過程中不可能完全消除,人們之所以能夠掌握眼前事物
的意義皆是仰賴於人們成見的幫助。
另一方面,除了否定追求客觀的可能性外,高達美亦認為詮釋學是不該被
方法所限制的,其表示一旦詮釋學被方法所局限,則這些方法會形成一道高牆,
詮釋學會無法衝破牆面來獲得詮釋對象的新義,其恩師海德格亦曾說道:「方法
的遵循是極為腐敗和墮落之路」。(Martin Heidegger, 1985)
若以方法去詮釋作品,在探討作品之前,詮釋者的思考方向便已被方法限
制,因此方法也限制了作品的真理,但人能夠限制、規定作品的意義嗎?詮釋者
並非為神,顯然來說,其沒有規定、限制真理的能耐,他們只能發現作品的真理,
並如實說出它,就像高達美所表示的,回歸到作品自身去理解其真理,而若要做
到這點,則詮釋學不能受方法所限制。
但這卻不意味著詮釋學會受到相對主義的亂象所挑戰,高達美認為,詮釋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