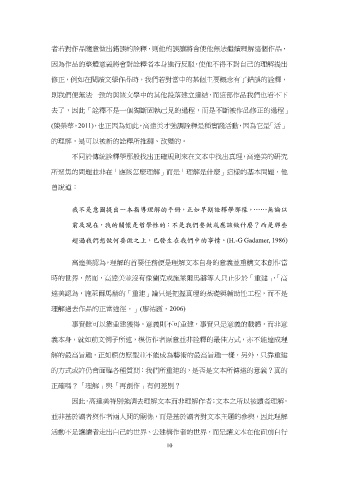Page 505 - 107學年度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畢業專題發表會「向。哲光」
P. 505
者若對作品隨意做出錯誤的詮釋,則他的誤讀將會使他無法繼續理解這個作品,
因為作品的整體意義將會對詮釋者本身進行反駁,使他不得不對自己的理解提出
修正,例如在閱讀文學作品時,我們若對當中的某個主要概念有了錯誤的詮釋,
則我們便無法一致的與該文學中的其他段落建立連結,而這部作品我們也看不下
去了,因此「詮釋不是一個獨斷固執己見的過程,而是不斷被作品修正的過程」
(陳榮華,2011),也正因為如此,高達美才強調詮釋是種實踐活動,因為它是「活」
的理解,是可以被新的詮釋所推翻、改變的。
不同於傳統詮釋學那般找出正確規則來在文本中找出真理,高達美的研究
所聚焦的問題並非在「應該怎麼理解」而是「理解是什麼」這樣的基本問題,他
曾說道:
我不是意圖提出一本指導理解的手冊,正如早期詮釋學那樣。……無論以
前及現在,我的關懷是哲學性的:不是我們要做或應該做什麼?而是那些
超過我們想做何要做之上,已發生在我們中的事情。(H.-G Gadamer, 1986)
高達美認為,理解的首要任務便是理解文本自身的意義並重構文本創作當
時的世界,然而,高達美並沒有像蘭克或施萊爾馬赫等人只止步於「重建」,「高
達美認為,施萊爾馬赫的「重建」論只是把握真理的基礎與輔助性工程,而不是
理解過去作品的正當途徑。」(廖祐震,2006)
事實雖可以靠重建獲得,意義則不可重建,事實只是意義的載體,而非意
義本身,就如前文例子所述,模仿作者原意並非詮釋的最佳方式,亦不能達成理
解的最高旨趣,正如模仿原型並不能成為藝術的最高旨趣一樣,另外,只靠重建
的方式或許仍會面臨各種質問:我們所重建的,是否是文本所傳達的意義?真的
正確嗎?「理解」與「再創作」有何差別?
因此,高達美特別強調去理解文本而非理解作者;文本之所以被讀者理解,
並非基於讀者與作者兩人間的關係,而是基於讀者對文本主題的參與,因此理解
活動不是讓讀者走出自己的世界、去建構作者的世界,而是讓文本在他面前自行
10